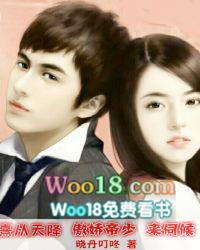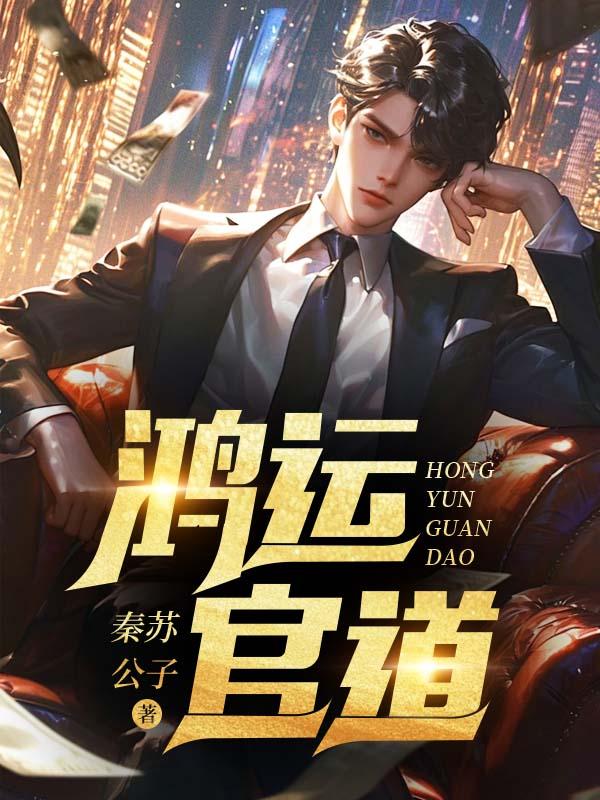精英小说网>子不类父?爱你老爹,玄武门见! > 第二百六十章 九重门(第1页)
第二百六十章 九重门(第1页)
有谚云:“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锅盔睡。”
但元狩三年腊月的雪显然下过了头,惊雷之后,关中连下了两场暴雪,将小麦厚厚地盖在了下面。
所幸,在这一年最冷之际,天上的云薄了,时或还能看见月亮。。。
海风卷着咸腥的气息拂过崖顶,少年赤足站在礁石边缘,衣袂翻飞如旗。他望着远处长安方向的天际线,那里灯火连成一片,仿佛星河坠入人间。铁券沉入深海的那一瞬,他忽然觉得胸口压了二十年的石头裂开了一道缝,透进一丝久违的光。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不再执着于寻找答案。他曾以为血脉决定了命运,可如今才明白,真正决定一个人的,是他选择走向何方。
与此同时,长安城内,明政院天文台新落成的穹顶之下,刘进正俯身注视着一架铜制望远镜。这是工匠们依照希腊手稿与西域传来的图纸反复试验三年才制成的奇器,镜筒长达七尺,底座镌刻着《太初历》节气图与二十八宿方位。今夜是“岁星守心”之象,群臣皆言此为帝王受难之兆,唯独刘进命人架起望远镜,亲自观测。
“陛下,真要在此时验证?”司天监老臣颤声问。
刘进未答,只将眼凑近目镜。刹那间,他瞳孔微缩??那颗被古人称为“荧惑”的火星,并非浑圆如珠,竟有极细微的沟壑纹理,宛如大地上的河川!而其侧还有一对极小的光点,若隐若现,似卫星绕行。
“原来如此。”他轻声道,“所谓‘荧惑守心’,不过是星辰运行之常。它们没有意志,更不会降灾。是我们的眼睛太浅,把自然当作了神谕。”
他直起身,环视满堂惊愕的官员:“从今日起,天文台每月发布《观星实录》,凡所见星体轨迹、日月食刻、彗出现象,皆以实测为准,不得附会谶纬。若有胆敢伪造天象、蛊惑民心者,按《求真令》斩首示众。”
话音未落,殿外急报再至。
“南海郡急奏!番禺海港突现巨舟残骸,长约百丈,通体漆黑,非木非铁,上有奇异铭文,形似蝌蚪,无人能识。更有尸首十余具冲上岸滩,肤白如雪,发色金红,貌不类中土之人。”
刘进眉头一动,心中忽有所感。他记得青鸾曾提过南越古籍中的传说:海外有“西夷之国”,乘巨舰横渡沧海,携火器而来,毁城灭族,后遭天雷击沉,全军覆没。难道……真有其事?
他当即下令:“封锁海岸,严禁百姓靠近;召明政院语言科、工器科、医正司即刻前往勘察;另派使者持《万国译语》赴西域,请大秦(罗马)商人辨认铭文。”
三日后,第一批勘验报告送抵御前。
“巨舟材质乃一种未知合金,熔点极高,断裂处呈蜂窝状结构,似经猛烈爆炸所致;船上器械残件中有类似‘霹雳火筒’之物,但构造远胜我朝火器;死者体内检出大量汞与铅毒,疑长期服用丹药所致;至于铭文……”记录官顿了顿,“经大秦商贾辨认,乃是拉丁文字,意为‘**ImperiumAeternumNautaeSolisOccidentalis**’??西方太阳帝国之航海军团。”
刘进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他们也是追寻永生的人。”
他知道,在遥远的西方,也有人试图用权力与科技对抗死亡。但他们走错了路??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妄图凌驾于天地之上。而这艘沉船,正是狂妄的代价。
他提笔写下批语:“存档备查,永不启用其技。然其所携知识,可为我所用。设‘异域格致馆’,专研其物理、化学、机械之理,但禁炼丹、禁拜神、禁以人为祭。”
与此同时,西域传来新的消息。
蓝氏城已改称“明理城”,成为西陲明政总会核心所在。青鸾主持编纂的《西域风物志》正式刊行,书中不仅记载各国地理风俗,更首次提出“气候带”概念,解释为何疏勒干旱而龟兹多雨。她还推动女子入学,设立“织锦学堂”,教授数学与纺织工艺结合之道,使丝绸产量提升三成。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一名来自康居的游方僧人在市集宣讲:“紫阳虽灭,真主未亡。李广逸早已转世为婴,藏于昆仑深处,待三十年后重临人间,开启永恒之门。”短短半月,竟聚众数千,甚至有明政学子动摇。
青鸾闻讯,亲赴集会。
她不带护卫,只携一名盲眼学生同行。那人虽不见光明,却精通声律与逻辑,曾在辩政会上驳倒七位博士。
面对狂热人群,青銮立于高台,朗声道:“你说李广逸转世?可有证据?”
“梦中得启示!”信徒高呼。
“那你梦见他吃米饭还是羊肉?穿丝绸还是麻布?左耳有没有痣?”她冷笑,“若连这些细节都说不出,凭什么说你见的是真人?不过是你心里想要一个救世主罢了!”
人群骚动。
她又指向那盲生:“这位同学从未见过阳光,但他知道太阳存在,因为皮肤能感受到温暖,植物需要它生长。这才是真实的认知方式??靠观察、推理、验证,而不是做梦!”
随即,她命人抬出一口大锅,现场演示如何用凸透镜聚焦日光点燃干草。“你们所谓的‘神迹’,不过是掌握了自然之理的人做的实验。我不否认世上仍有未知,但正因为未知,我们才更要学习,而不是跪下!”
信徒们面面相觑,终有人悄然离去。
当晚,青鸾收到一封匿名信,字迹歪斜,墨色陈旧:
>“你不该烧毁祖祠莲花。
>不该熔笛为铃。